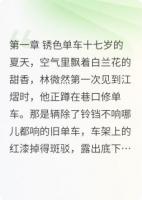第一章锈色单车十七岁的夏天,空气里飘着白兰花的甜香,林微然第一次见到江熠时,
他正蹲在巷口修单车。那是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单车,车架上的红漆掉得斑驳,
露出底下青灰色的铁,像块生了锈的疤。江熠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到肘弯,
露出小臂上淡青色的血管,他手里捏着扳手,额角的汗顺着下颌线往下掉,
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洇成一小片深色。林微然抱着刚买的画纸经过,
被单车链条卡住的“咔嗒”声绊住脚步。她看了会儿,忍不住小声说:“链条歪了,
得先把后轮松一点。”江熠抬头时,阳光正从他身后的老梧桐叶隙里漏下来,
在他眼里碎成一片金芒。他愣了愣,喉结动了动:“你会修?”“我爸以前是修单车的。
”林微然蹲下身,指尖避开链条上的油污,轻轻拨了拨变形的链扣,“这里卡太紧了,
得用螺丝刀撬一下。”江熠递过螺丝刀,目光落在她手上。那是双很干净的手,
指甲修剪得圆润,指腹上沾着点水彩颜料的淡痕,和他满是油污的手放在一起,
像两截不同世界的枝桠。单车修好时,林微然的指尖也沾了点黑,她不在意地蹭到牛仔裤上,
站起身说:“好了,试试?”江熠跨上去蹬了两下,链条顺畅地转起来,他回过头冲她笑,
嘴角咧开个大大咧咧的弧度,露出两颗小虎牙:“谢了,我叫江熠,三中的。”“林微然,
一中的。”她抱着画纸往后退了退,白兰花的香气漫过来,混着他身上淡淡的汗味,
奇异地让人安心。后来林微然才知道,江熠是巷尾废品站老板的儿子,
父母在他十岁时出了车祸,只留他和奶奶相依为命。他总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
却总把自己收拾得干净,那辆锈色单车是他从废品堆里捡来修的,
每天骑着它穿梭在老城的巷弄里,帮奶奶收废品,顺便送几份外卖。
他们的交集像那辆单车的链条,磕磕绊绊却总也断不了。林微然会在放学后绕到巷口等他,
有时递上一瓶冰镇汽水,有时是块刚买的绿豆糕;江熠则会在她画画到天黑时,
骑着单车跟在她身后,车铃“叮铃铃”地响,像在说“别怕,我在”。
有次林微然画巷口的老槐树,画到一半下起了雨,她没带伞,抱着画板往家跑,
江熠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罩在她头上。“别淋湿了画。”他只穿件背心,
雨水顺着他利落的短发往下淌,却笑得一脸灿烂。衬衫上有淡淡的肥皂味,混着雨水的凉,
林微然的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她偷偷抬眼,看见他脖颈上的水珠滑进锁骨,
那里的皮肤在雨里泛着冷白的光。那天之后,江熠的单车后座多了块软垫,
是林微然用碎布头缝的。他载着她穿过铺满夕阳的巷弄,风掀起她的长发,扫过他的脸颊,
他总会故意拐个弯,听她惊惶又带着笑的尖叫。林微然的画里开始出现江熠的影子。
晨光里他扛着废品麻袋的背影,暮色中他靠在单车旁抽烟的侧颜,甚至是他修单车时,
沾了油污的指尖。她把这些画藏在画夹最底下,像藏着个甜得发腻的秘密。高三那年冬天,
江熠奶奶突发脑溢血住院,手术费像座大山压下来。他退了学,白天在工地扛钢筋,
晚上去夜市摆摊卖袜子,那辆旧单车成了他运输货物的工具,车后座绑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在寒风里摇摇晃晃。林微然拿着自己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去找他时,
他正在夜市的路灯下数零钱,手指冻得通红,指尖裂了好几道口子,渗着血丝。
“这点钱不够。”他把钱推回来,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你好好考大学,别管我。
”“江熠,”林微然把钱塞进他口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可以去**,我们一起凑。
”“不用。”他别过脸,路灯照在他脸上,能看到颧骨上冻出来的红,“我这种人,
配不上你考大学的路。”那天晚上,林微然看着江熠骑着单车消失在巷口,
车后座的蛇皮袋撞在车架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在敲她的心脏。她站在原地,
直到寒气钻进骨髓,才发现手里还攥着给他织了一半的围巾,藏蓝色的毛线,
是他最喜欢的颜色。第二章褪色围巾林微然考上南方的大学那天,江熠来送她。
他还是那辆旧单车,只是车后座的软垫换成了新的,用深蓝色的帆布缝的,针脚歪歪扭扭,
一看就是他自己缝的。他穿着件新的黑夹克,头发剪得很短,眉眼间的少年气淡了些,
多了点沉郁的轮廓。“恭喜。”他递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有零有整,
纸币边缘都磨得发毛,“我凑的,够你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林微然没接,
眼圈红了:“你留着给奶奶治病。”“奶奶好多了。”江熠把布包塞进她行李箱侧袋,
手指碰到她的手背,像碰了块冰,猛地缩了回去,“我找了份修车行的工作,能挣钱了。
”火车开动时,林微然趴在车窗上看他。江熠站在月台上,没挥手,也没说话,
就那么望着火车,直到他的身影缩成一个小黑点,被铁轨尽头的雾气吞掉。她摸出那个布包,
打开时掉出一张纸条,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别省钱,按时吃饭。”大学四年,
他们的联系靠书信和偶尔的电话维持。林微然寄给他的信里,夹着南方的木棉花瓣,
写着美术系的趣事,画着校园里的香樟树;江熠的回信总是很短,说奶奶的近况,
说修车行的生意,说巷口的老梧桐又落了多少叶,末了总加一句“钱够不够,不够我再寄”。
林微然知道他嘴硬。有次她放假偷偷回了趟老城,在修车行门口站了很久,
看见江熠蹲在地上修一辆重型摩托车,排气管烫得发红,他不小心碰到,
手背瞬间起了个水泡,他只是咬着牙抹了点牙膏,继续手里的活。她没上前,
躲在树后哭了半场,回学校后,把自己得奖的奖学金全寄给了他,附言说“是画稿的稿费,
不缺钱”。毕业那年,林微然收到江熠的信,说奶奶走了。信很短,
只有一句话:“她走的时候,说想看看你画的画。”林微然买了最快的火车票回去。
老城的巷口还是老样子,只是废品站的门关了,修车行里,江熠坐在地上,背靠着墙,
怀里抱着奶奶的遗像,面前摆着她寄给他的所有画,一张一张,都用牛皮纸包着,整整齐齐。
“你回来了。”他抬头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像只困在笼子里的兽,“我没照顾好她。
”林微然蹲下来,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机油味,混着淡淡的烟草味。
她想说“不是你的错”,却被他推开。“微然,”他看着她,眼神里有她看不懂的挣扎,
“我们不一样。你该留在南方,找个画画的工作,嫁个有文化的人,
而不是回来守着我这个修车的。”“我不介意。”林微然抓着他的手,那双手布满老茧,
指关节粗大,掌心还有没褪掉的疤痕,“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介意。”他甩开她的手,
声音冷得像冰,“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连你买颜料的钱都凑不齐,你跟着我,只会受苦。
”那天晚上,林微然在巷口的旅馆住下。凌晨时,她听见窗外有动静,拉开窗帘,
看见江熠站在楼下,手里拿着她当年没织完的那条藏蓝色围巾,他在寒风里,
一针一线地往下织,笨手笨脚,线缠成了一团,他却没停,直到天快亮时,
才把那条歪歪扭扭的围巾挂在她的门把上。林微然拿着围巾,站在空无一人的巷口,
看着江熠骑着那辆旧单车消失在晨雾里,车铃“叮铃铃”地响,像在说“别等了”。
第三章药味晨昏林微然最终还是留在了南方,进了一家美术馆工作。她很少再回老城,
只是偶尔会在画里画出那条巷弄,画里的少年蹲在地上修单车,阳光落在他的发梢,
像镀了层金。同事给她介绍对象,是个温文尔雅的策展人,叫顾明宇,懂她的画,
也欣赏她的才华。他会带她去看画展,去听音乐会,在她加班时送来热咖啡,说“微然,
荷花能干2025-06-27 21:34:24
江熠跨上去蹬了两下,链条顺畅地转起来,他回过头冲她笑,。
 豪门后妈,专治不服
豪门后妈,专治不服我或许还能让你过得舒服些。」「你要是再敢对我动手,或者说一句不干不净的话……」我蹲下身,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看着我的眼睛。「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我的眼神很冷,冷得像冰。林薇薇被我吓住了,她看着我,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她哭着问。「我想
作者: 吸金光环言情已完结 梁千洛周战北
梁千洛周战北我是大院里的营长夫人,也曾是大周朝垂帘听政的皇后。一次穿越,我成了现代人。原以为有了一夫一妻制,我这辈子终于不用再勾心斗角,过安生日子。直到父亲牺牲后
作者: 小说家都市连载中 夏瑾萧叙
夏瑾萧叙5月6日,是夏瑾的排卵日。萧叙特意从香港飞了回来。晚上的卧室热烈滚烫。夏瑾面目潮红,双目迷离地看着上方动作的男人,他肤色冷白,五官清俊,
作者: 小说家都市连载中 销冠的我年终奖五千,泡茶的同事拿五万
销冠的我年终奖五千,泡茶的同事拿五万占了我全年业绩的近一半。李总这个人,脾气出了名的古怪,极度注重细节,而且只认人,不认公司。当初为了拿下他,我陪着他跑了三个城市的工厂,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做的项目方案修改了不下二十遍,甚至连他秘书的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赵凯?他连李总喝茶喜欢放几片茶叶都不知道。我对着电话,语气平静:“李总,
作者: 知心o言情已完结 亲妈二婚后,新家使用手册
亲妈二婚后,新家使用手册亲妈二婚后,梁宴舒多了四个新家人。沉稳憨厚很爱妻的继父,爱作妖的奶奶,雷厉风行的律师小姑,个性内敛的弟弟。第一次遇见林硕,梁宴舒觉得他是个人美心善的帅哥。第二次见面,才发现他是那个“难搞”的甲方客户。再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渊源竟追溯到十几年前……再次遇到梁宴舒,林硕不知不觉融入了这个六口之家的生活。嗯,虽然鸡飞狗跳,但很有意思。
作者: 简至夏言情连载中 钟离云峥谢雨昭
钟离云峥谢雨昭“云峥,妈找了你7236天,终于找到你了!”万寿园陵墓,一个身着华丽的贵妇紧紧拉着我的手,哭成了泪人。“你走丢的这些年,爸妈一直在全世界各地找你,每一天都是痛苦的煎熬。如今终于找到你了,现在你养父母的后事也都处理完了,你愿意和爸妈一起去香港生活吗?”听着母亲满是期盼的问询,我看了看墓碑上笑容和蔼的中年男女,红着眼没有做出决定。“我会好好考虑。”短时间内,我还不适应从普通男孩变成亿万富豪亲生儿子的身
作者: 小说家都市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