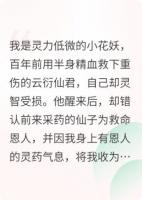
我是灵力低微的小花妖,百年前用半身精血救下重伤的云衍仙君,自己却灵智受损。
他醒来后,却错认前来采药的仙子为救命恩人,并因我身上有恩人的灵药气息,将我收为替身侍女,时时嘲讽我“东施效颦”。
直到他的“恩人”仙子需要一味花妖心血入药,他命我剜心献祭。
我笑着问他:“仙君,若救你的人是我,你可会有一分愧疚?”他答:“笑话,凭你也配?”
我当着他的面散尽修为,涅槃重生,恢复了百年前的真实身份——上古花神转世。
我转身接受了药神谷百年来的诚挚求婚。
大婚当日,云衍仙君终于冲破记忆封印,手持我当年破碎的本命花瓣,疯魔般闯进仙界盛典,震碎我的凤冠:“谁准你嫁他人?!”
而这一次,护在我身前的,是整个药神谷。
……
我是三界最卑微的一株汀兰小花妖,至少,在云衍仙君眼中是如此。
此刻,我正跪在云澜仙府冰冷刺骨的琉璃地面上,双手捧着一盏滚烫的云雾茶。
氤氲的热气熏得我眼睛发涩,却不敢有丝毫晃动。
上首,那个我耗费半身精血从幽冥边缘拉回来的男人,正慵懒地倚在云锦软榻上,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扶手。
他周身流转的仙辉,与我身上黯淡的妖气,隔着不过数丈距离,却仿佛横亘着无法逾越的天堑。
“蠢笨的东西,连盏茶都奉不好。”他未曾抬眼,清冷的声音却像淬了冰的刀子,精准地扎进我心口,“这云雾茶最重火候,过了时分,便失了几分灵气,与你一般,徒有其表,败絮其中。”
我垂着头,看着杯中自己模糊的倒影,一张清秀却苍白的面容,眼底是百年磋磨留下的麻木。
百年前,我还只是深山里一株懵懂修炼的汀兰,灵智初开,心思纯净得像山涧最清澈的泉水。
那日,天际划过一道染血的金光,坠落在我身旁。
我看到了他,云衍仙君,仙界赫赫有名的战将,浑身是血,仙源破碎,气息奄奄地躺在我的花枝旁。
那惊心动魄的俊美,即使被重伤和血污掩盖,也足以让天地失色。
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或许是妖类对强大生灵本能的敬畏,又或许是……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惜。
我做出了修炼以来最愚蠢,也最义无反顾的决定。
用我近半的本命精血,混合着与生俱来、连自己都不明所以的微弱治愈之力,一点点滋养他破碎的仙源。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如同将自身神魂寸寸剥离。
我耗尽了积攒百年的微末灵力,灵智因此受损,修为几乎倒退至原形,才勉强吊住了他一线生机。
昏迷前,我将自己最珍贵的一瓣本命花蕊,悄然放在他心口,以期能继续温养他的伤势。
我以为,救了一个了不起的仙人,是做了一件好事。
却不知,这将是我百年噩梦的开端。
他醒来时,我因灵力枯竭和灵智受损,化回原形在一旁沉眠恢复。
恰逢那位采药的芷晴仙子途经此地,发现了重伤初愈的云衍仙君,以及他身边萦绕的、属于我的那独特治愈气息的残余。
于是,顺理成章地,芷晴仙子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而当我勉强恢复人形,循着与他之间那点微弱的精血联系,跌跌撞撞找到金碧辉煌的云澜仙府时,等待我的,不是感激,而是他审视而冰冷的目光。
“你身上为何有芷晴的灵药气息?”他蹙眉,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小小花妖,也敢觊觎仙君?莫非是想效仿恩人,来个东施效颦?”
东施效颦。
这四个字,像烙印,刻在了我之后百年的生命里。
他因我身上那抹源自本命花蕊、与芷晴仙子接触后残留的相似气息,认定我心怀不轨,却又因这气息能奇异地缓解他旧伤偶尔带来的隐痛,便将我留在府中,给了个“替身侍女”的身份。
美其名曰:赎罪,洗刷我“冒充”恩人的罪孽。
百年间,我为他烹茶煮酒,打理药圃,忍受着他忽如其来的挑剔与嘲讽。
他心情好时,会看着我的脸出神,透过我,看着另一个被他放在心尖上的人。
他心情不好时,我便成了他所有烦躁的宣泄口。
“收起你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芷晴心地善良,可不似你这般矫揉造作。”
“能留在云澜仙府,是你几辈子修来的造化,安分守己,或许本君能容你多活几日。”
我曾试图解释,磕磕巴巴,语无伦次,提及那瓣本命花蕊。
他却只当是我新的攀附手段,冷笑一声:“凭你也配凝聚本命花蕊?撒谎成性,罪加一等。”
后来,我便不再说了。
灵智受损让我反应总是慢半拍,记忆也混沌,很多前尘往事都模糊不清,唯独救他那日的痛楚,和这百年的屈辱,清晰得如同昨日。
就在我捧着茶盏,手臂开始微微颤抖时,一道娇柔的声音打破了凝滞。
“云衍哥哥!”
芷晴仙子身着霓裳,翩然而至,很自然地挨着云衍坐下,目光扫过我时,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和得意。
“哟,这小花妖又惹你生气了?”她嗓音甜美,说出的话却如针尖,“总是不懂规矩,也难怪,山野小妖,能指望她有什么见识。”
云衍仙君的脸色稍霁,语气是面对我时从未有过的温和:“无妨,不必为她败了兴致。你今日气色似乎不大好,可是旧疾又犯了?”
芷晴仙子顺势轻蹙眉头,弱不禁风地倚向他:“是有些……心口闷得慌。前日去拜访药神谷的岐黄仙翁,他说……他说若有一味至纯至净的花妖心血作为药引,或可根治我这顽疾。”
花妖心血?
我手一抖,盏中滚烫的茶水险些溅出。
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
云衍仙君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不再是平日的冷漠或嘲讽,而是一种权衡利弊的审视,如同在看一味……药材。
他沉吟片刻,开口,声音没有半分波澜:“既是如此,眼前不正好有一个现成的?”
他指向我,语气随意得像在决定一株草的命运。
“汀兰,三日后,你便剜出心血,为芷晴入药。”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琉璃盏的温热透过掌心,却暖不了我瞬间冰凉的心脏。
百年屈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看着他那张俊美无俦,却冷漠至极的脸,百年来的隐忍、恐惧、卑微,在这一刻,奇异地化作一片死寂的平静。
我慢慢抬起头,第一次,毫无畏惧地直视他那双深邃如星海,却从未映出我真实倒影的眼眸。
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极淡、极诡异的弧度。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又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大殿里。
“云衍仙君。”
“若我说,百年前,耗尽半身精血救你的人,其实是我……”
“你可会,有哪怕一分一毫的愧疚?”
过时有秀发2025-10-20 14:41:36
我以为,救了一个了不起的仙人,是做了一件好事。
老虎娇气2025-09-24 23:58:52
更不配,用我这上古花神之心血,去救一个心思龌龊的假仙子。
冰棍含蓄2025-09-26 05:34:49
我微微侧头,看见一个身着青色药童服饰的少年站在不远处,手中还捧着一只氤氲着白气的玉碗,眼神清澈,满是关切。
 人人都说我是疯子,我却把义妹嫁入豪门
人人都说我是疯子,我却把义妹嫁入豪门眼神陌生得仿佛在看一个魔鬼。许久,她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是。”我松开手,像甩开什么垃圾。“滚出去。”江柔踉跄着,逃也似的离开了我的房间。世界终于清静了。我坐回床上,却毫无睡意。傅斯年的出现,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一个我完全无法掌控的变数。我必须弄清楚,他到底想干什
作者: 老宋大妈言情已完结 祝君良缘,我嫁早逝储君
祝君良缘,我嫁早逝储君“这钱”“该得的。”沈执看着我的花店,转移了话题,“生意怎么样?”“还好,刚起步。”我们聊了几句,气氛有些尴尬。沈执似乎不擅闲聊,很快便告辞离开。林晓凑过来,眨着眼睛问:“晴姐,那是谁啊?好有气质!”“一个老朋友。”我轻描淡写地带过,心里却泛起涟漪。之后几个月,沈执偶尔会来花店,有时买束花,有
作者: 亮眼的咸鱼言情已完结 帝阙缠:太后不承让
帝阙缠:太后不承让谈何容易。顾丞相的案子尘埃落定后,宫中渐渐恢复了平静。萧彻却比往日更加繁忙,既要整顿朝堂秩序,又要处理顾丞相留下的烂摊子,常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日抽空来长乐宫请安。这日傍晚,萧彻又来了。他坐在桌前,疲惫地揉着眉心。我端来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中:“陛下辛苦了。”他接过茶,喝了一口,眼中闪
作者: 减肥是人类的大忌言情已完结 我的生死与悲欢,在他眼里无足轻重
我的生死与悲欢,在他眼里无足轻重嫁给他五年,我从未成为能让他破例的人。新年招待会,他说我的旗袍不合时宜;异国被劫,他让我按流程联系警卫队;弟弟在战乱区失联,他坚持“非建交地区通讯需中转”的公约。我当掉所有嫁妆,在黑市雇车队找回弟弟时,他已因感染奄奄一息。当我抱着弟弟冰冷的身体回到使馆,他刚批下的救援许可才姗姗来迟。看着我隆起的腹部,我终于明白,在他恪守的“规矩”与“国际公约”
作者: 杨枝甘露言情连载中 沈书宁秦霁川
沈书宁秦霁川秦霁川出轨被曝光的那天,我差点一尸两命。后来,他的小情人官宣结婚,而我官宣离婚。……狗仔怕我一尸两命,在我生产后,才曝光了我丈夫秦霁川出轨当红小花的事。堂堂秦氏集团的总裁,怕小白花被伤害,连夜将人送去了爱尔兰。“都是那些狗仔乱发的,根本没有出轨的事。”秦霁川站在病床前,没有对我刚生产完的心疼,只有轻描淡写的解释。我眸中平静,将一叠照片扔在了他面前,照片上,清晰地拍下了秦霁川和小白花宋曼出入各种场所
作者: 大神都市连载中 他给了我一张新脸,让我亲手狩猎背叛者
他给了我一张新脸,让我亲手狩猎背叛者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耳钉里,只有我自己沉重的呼吸声。顾言,你在听吗?你一定要在外面啊。不知过了多久,门终于开了。走进来一个男人。他大概四十多岁,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中式盘扣褂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文儒雅,像个大学教授。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身份,我绝不会把眼前这个人,和那个变态的“藏品”收藏家联系
作者: 纯美式言情已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