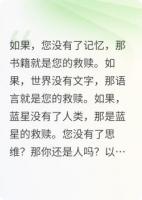如果,您没有了记忆,那书籍就是您的救赎。如果,世界没有文字,那语言就是您的救赎。
如果,蓝星没有了人类,那是蓝星的救赎。您没有了思维?那你还是人吗?以上都没有哪?
这,就是末世,人类的末世。蓝星的救赎。防空洞的铁门在身后发出锈蚀的**,
阿砚把最后一块砖嵌进门缝,指尖被边缘的铁刺划开细口,血珠渗出来,
在昏暗的光线下像颗凝固的火星。他低头看了看,没有痛感——不是麻木,
是身体已经忘记了“痛”这个词该配什么样的神经反应。洞壁上挂着块铁皮,
是他三年前从废弃公交站拆来的。他曾用烧黑的木炭在上面写过字,
现在那些笔画都褪成了淡灰色的影子,像被雨水泡烂的蛛网。
他记得自己写过“防空洞”三个字,写的时候手指在铁皮上顿了三下,
想着万一哪天忘了这里是哪儿,好歹有个凭据。可现在他盯着那片模糊的痕迹,
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的风,吹过没有名字的旷野。角落里堆着他的“书”。
其实就是些装订成册的硬纸壳,有的是笔记本的残骸,有的是撕开的包装盒。十年前,
当“文字失效”刚开始蔓延时,他是古籍修复师,在市图书馆的地下室里,
亲手把一页唐代的《金刚经》托裱在桑皮纸上。那天下午,阳光透过气窗斜斜切进来,
他看着经卷上“如是我闻”四个字突然扭动起来,像被扔进水里的墨,洇开,淡去,
最后变成和纸一样的米白色。他伸手去摸,指尖只触到宣纸细微的纹理,
像摸到了时间的骨头。现在这些硬纸壳上,连墨的影子都没有了。他每天还是会翻开它们,
用指甲在空白处划,想刻下点什么。比如今天早上,他摸到防空洞外的蒲公英,
绒毛蹭在手上痒痒的,他想记下来,可指甲尖在纸壳上划出的只有歪歪扭扭的曲线,
像条找不到家的蚯蚓。“呜……”洞口传来微弱的响动,不是风。
阿砚抄起身边的钢管——那是他从消防栓上拧下来的,
管身上原本印着的“消防”二字早就化了,现在就是根冰冷的铁。他贴着洞壁挪过去,
透过砖缝往外看。是个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件过大的条纹衬衫,袖口磨得卷了边。
她蹲在蒲公英丛里,用小手捏着绒毛球,一吹,白色的小伞就飘起来,
有的粘在她乱蓬蓬的头发上。她看见阿砚的砖缝,没害怕,反而咧开嘴笑了,
露出两颗缺了角的门牙。阿砚把钢管放下了。这三年,
他见过太多“空壳”——那些眼神发直,只会重复同一个动作的人。
他们会对着断墙发呆一整天,或者反复拧一个没有水的水龙头。但这个孩子的眼睛里有光,
像他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萤火虫,藏在稻禾丛里,忽明忽暗。孩子朝他伸出手,掌心摊开,
里面是颗野草莓,红得发紫,沾着点泥土。她发出“啊……甜”的音,单音节,
拖着点模糊的尾音,像被露水打湿的琴弦。阿砚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他想起母亲。
母亲走的那年,语言已经开始“生锈”了。她躺在床上,指着窗外的夕阳,想说什么,
张了张嘴,最后只发出“暖……”的声音。那时候母亲的手还能握住他的手,
掌心的温度像块慢慢冷却的炭。他接过野草莓,塞进嘴里。酸和甜炸开的瞬间,
记忆突然冒了个尖——小时候母亲把草莓榨成汁,装在玻璃瓶里,
瓶身上贴着她写的“甜”字。那时候字还活着,笔画像串起来的星星。孩子看着他吃完,
又笑了,这次她指着天上的云,说:“白……飘。”阿砚点点头,想说“云”,
但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只能发出“嗯”的音。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名字,是母亲取的,
叫“砚”,说他出生那天,父亲在书房研墨,砚台里的墨汁映着月亮。
可这名字太久没人叫过了,他几乎要忘了舌尖抵住上颚发“y”音的感觉。“你……叫什么?
”他试着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孩子眨眨眼,好像没听懂。
她捡起块黑色的木炭——是阿砚昨天烧火剩下的,在地上画起来。先画了个圆圈,
然后在圆圈周围画了好多短线,像太阳。接着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
旁边画了个更大的人,手拉手。阿砚蹲下来,看着她画。木炭在地上划过的声音,沙沙的,
像他以前翻书的声音。他突然想,或许文字没死,只是换了种样子活在地上。“小星。
”他指着天上的星星,又指了指她,“你叫小星,好不好?”孩子还是眨眨眼,
但这次她跟着他的口型,模仿着发出“星……”的音,虽然很轻,像片羽毛落在水面上。
这时候,从街角跑过来一只狗。黄棕色的毛,瘦得能看见肋骨,但眼睛很亮。
它跑到小星身边,用头蹭她的裤腿,尾巴摇得很用力。“老黄?”阿砚愣了一下。
这狗他见过,三年前在图书馆门口,他喂过它半块压缩饼干。那时候它脖子上还挂着个牌牌,
上面有字,他当时还能看懂,是“导盲犬大黄”。现在牌牌早就没了,它也老了,
眼角堆着浊物,但看见阿砚,尾巴摇得更欢了。老黄突然朝着防空洞的方向吠了两声,
然后咬住小星的裤脚往洞里拽。阿砚心里一紧,抬头看天。天边的云开始变颜色,
不是夕阳的红,是种灰绿色,像馊了的菜汤。是“蚀忆雾”。他拉着小星往洞里跑,
老黄跟在后面,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刚钻进洞口,阿砚就听见外面传来“咚”的一声,
像是什么重物倒了。他回头看,砖缝外,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直挺挺地跪在蒲公英丛里,
手里还攥着根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雾越来越浓,已经能看见老头的头发在雾里慢慢变灰,
像被撒了把面粉。小星往阿砚身后缩了缩,抓住他的衣角。阿砚把她搂进怀里,
闻到她头发上的蒲公英味。他想起母亲说过,雾会吃掉记忆,先是最近的,再是以前的,
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母亲走的前一天,已经不认识他了,只是摸着他的脸,
反复说“暖……”洞里的光越来越暗,只有铁皮缝隙透进来的一点灰绿色。老黄趴在地上,
把头埋进前爪里。小星从阿砚怀里探出头,拿起地上的木炭,在他手背上画了个太阳。很烫。
阿砚低头看着手背上的太阳,突然觉得眼眶有点湿。他已经很久没哭过了,
连“哭”这个动作都快忘了。他抬手,用粗糙的拇指蹭了蹭小星的头发,这次他没试着说话,
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老黄突然抬起头,朝着洞深处叫了一声。阿砚顺着它看的方向,
洞的尽头,堆着他搜集来的书。那些曾经被称为《诗经》《史记》《天工开物》的东西,
现在就是一堆堆印着模糊痕迹的纸。但在最上面,他看见了那本没修复完的《金刚经》,
米白色的宣纸在昏暗中,像片安静的月光。他突然想,或许“救赎”从来就不在书里,
也不在话里。小星的手很暖,老黄的呼吸很稳,手背上的太阳还在发烫。阿砚闭上眼睛,
听着洞外蚀忆雾流动的声音,像潮水,一波一波地漫过城市的骨头。
他好像又听见了母亲的声音,不是“暖”,是很多年前,她抱着他,指着书里的字,
一个一个地念:“人……之……初……”虽然他已经忘了那些字的样子,
但舌尖好像还留着发音时的温度。蚀忆雾退去时,天是洗过的铅灰色。
阿砚推开防空洞的砖缝,铁锈味混着潮湿的泥土气涌进来,呛得他咳了两声。
小星趴在老黄背上睡着了,嘴角还沾着点野草莓的红渍,手背上的木炭太阳被汗水晕开了些,
像片融化的晚霞。老黄竖着耳朵,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见阿砚探头,
它用尾巴尖轻轻扫了扫小星的腿,像是在说“别吵醒她”。外面的世界被雾泡得发涨。
蒲公英丛倒了大半,沾着灰绿色的黏液,像被踩烂的鼻涕虫。穿蓝布衫的老头还跪在原地,
身子已经硬了,手指保持着握树枝的姿势,地上的划痕被雾水浸成了深色,弯弯曲曲的,
像条干涸的河。阿砚走过去,蹲下身看那些划痕——不是字,也不是画,
就是些无意识的乱撇,像婴儿挥舞的蜡笔。他想起十年前,书法课上,
老师总说“字是心画”,可现在,心空了,连划痕都成了无主的游魂。“阿……砚?
”小星醒了,揉着眼睛站在老黄身边。她在学他的名字,这两天总把“砚”发成“燕”的音,
舌尖抵着上颚,像含着颗糖。阿砚回头,看见她正指着老头的蓝布衫,眼里有困惑,
没有恐惧。她还不懂“死亡”,就像她不懂“文字”曾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走了。
”阿砚拉起她的手。她的手心有层薄茧,是抓木炭抓的,摸起来像块温凉的鹅卵石。
老黄叼起阿砚放在洞口的布包——里面装着半块压缩饼干,
还有那本被阿砚刻满指甲印的硬纸壳书——跟在他们身后。他们沿着断裂的柏油路走。
路两旁的店铺招牌都成了扭曲的金属骨架,曾经的“服装店”三个字,
现在只剩一根弯成“S”形的铁条,缠着几缕枯黄的爬山虎。五年前,这里还是热闹的,
语言刚退化时,人们会指着橱窗里的衣服“啊……穿”,用手势比划大小。
阿砚记得母亲在这里买过一件碎花衬衫,她当时说“好看”,后来变成“花……暖”,
最后连“花”都忘了,只摸着布料笑。“树……高。”小星突然停下,指着路边的悬铃木。
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枝桠已经戳破了旁边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绿色的叶子从破洞里钻进去,在空荡的楼层里铺成一片流动的绿。阿砚抬头,
看见阳光透过叶隙,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他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
他突然想起“参天”这个词,舌尖顶了顶牙龈,发不出音。文字死了,
连带着这些描绘世界的词,都成了喉咙里的石头。老黄突然加快脚步,
朝着前面的十字路口跑。阿砚跟过去,看见一家废弃的文具店,玻璃柜里还摆着几支蜡笔,
红的、黄的、蓝的,塑料外壳被晒得发脆,却依然亮得扎眼。小星挣脱阿砚的手,
扒着玻璃柜往里看,手指在“红”色蜡笔的位置画圈,嘴里发出“啊……火”的音。
阿砚用钢管敲碎玻璃,捡出那支红蜡笔。蜡笔的笔杆上原本印着“安全无毒”,
路人想人陪2025-07-17 00:27:36
他回头看,砖缝外,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直挺挺地跪在蒲公英丛里,。
 孕检报告?抱歉,打胎费我出了!
孕检报告?抱歉,打胎费我出了!你爸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家就完了啊!”苏晚握着手机,手脚冰凉。先是弟弟被开除,然后是父亲被调查。这一切,都发生在林辰的项目被她毁掉之后。难道……一个让她不寒而栗的念头,浮现在脑海。难道这一切,也和林辰有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辰只是一个程序员,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影响到纪委的调查?
作者: 大水的郭蔷薇言情已完结 学渣摊牌了,校花吓傻了
学渣摊牌了,校花吓傻了如果每个人都以‘这是特例’为借口来打破规则,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李思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台下,市一中的学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方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许佳她们都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跟睡着了一样。现在,轮到我这个四辩,做总结陈词了。所有人的
作者: 老鼠爱上咖啡猫言情已完结 遇事不决?查查攻略!
遇事不决?查查攻略!我穿越到了大夏仙朝,成了个声名狼藉的九皇子。可悲的是,我知晓自己是本玄幻小说里的炮灰,沉迷酒色、不学无术,不仅会被退婚,还会成为天命之子扬名立万的垫脚石,最终下场凄惨。就在我觉得命悬一线时“每日情报系统”突然激活。它带来的情报让我得知,那位被污蔑入狱的传奇女剑仙尚有生机。我决心冒险闯入镇魔狱救下她,获取她的无上剑道传承,以此逆天改命。从此,我不再
作者: 遮幕夜言情连载中 重生为霸总的白月光替身,我连夜买了去南极的机票
重生为霸总的白月光替身,我连夜买了去南极的机票\"这里是中山站,我们的家。你将负责与各国科考队联络,整理文献,可能还要教孩子们英语——站里有几个随父母来的学龄儿童。\"科考站比我想象的现代化。圆顶建筑群在雪地中延展,内部温暖明亮。我的宿舍很小,但有独立卫浴和小窗,窗外是皑皑白雪。\"明天开始工作,\"陈博士递给我日程表,\"今晚先适应环境。记住,极夜来了
作者: 菜头就是萝卜言情已完结 入赘三年当牛做马,觉醒神瞳后我让豪门跪下叫爷
入赘三年当牛做马,觉醒神瞳后我让豪门跪下叫爷你家那条废狗要是知道我们在他的车上弄,会不会气死?」「提他干什么,扫兴」那一刻,我感觉头顶绿得发慌,心里却出奇地冷静。原来如此。这就是你们看不起我的理由?行,既然老天给了我这双眼,这绿帽子,我不仅要摘下来,还要给你们每个人都戴上一顶!2晚上的拍卖会,灯红酒绿。我穿着一身廉价西装,跟个服务生似的
作者: 四眼笨狗言情已完结 闺蜜生日当天,丈夫和她给私生子办满月酒?
闺蜜生日当天,丈夫和她给私生子办满月酒?从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天色太过昏暗了,以至于我根本没看清男人拿的是什么。直到顾庭川伸手拉开了后座的门,那一瞬间我清楚的看到了男人手上的东西。他竟然……他竟然真的带来了父亲的骨灰!“下车。”见我始终沉默着没有动作,男人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只见他眉头一皱,下一秒却举起了手中的骨灰。我顾不上太多了,只是狼
作者: 甜玉米言情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