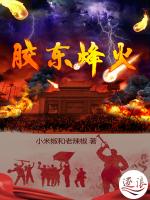
第一章:辫子
胶东半岛,千百年来就是山东人杰地灵的一块风水宝地,这里风光秀丽,民风淳朴,有山有水,相辅相成。
刘家庄镇,坐落在即墨县的最西北角,当地人称西北老洼地,这可是个土肥人美的好地方。他的身后就是蜿蜒流转的大沽河支流五沽河,河对岸分别与莱西的朴木镇和平度的仁兆镇隔河相望。从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刘家庄镇的最高行政长官一直由刘家庄的大户刘姓族长和他的族人轮番担任,别人无从插手。
光绪后期县里有人不服,从外面调进一个据说中过武举的人来刘家庄担任乡总,怎奈好景不长,不到半年他自己就挂冠跑了,连个理由都没给他的上峰留下。
从那以后刘家更以本土的土皇帝自居,不管是以前叫乡总也好还是现在改成镇长也罢,这里的最高长官成了他们刘家的世袭官位,不管谁来即墨上任也得高看他们刘家一眼,不然谁来做这个地方官也坐不安稳,那个武举人就是个例子。
镇公所就在官道南侧,最初是官家的驿站,后来被刘家几度重修扩建。现有正房五大间,配备南屋五间东厢房五间,院子南北长二十米,东西十五米。民团成立之后,刘家又把院墙以西一块自家的地拿出来,推平压实做成操场。
现任镇长也就是刘家的现任族长刘长卿,他爹死的早,按照族长只能由长子长孙接任的老规矩,刘长卿在他四十岁那年就出任了这个职位。刘家人通过一百多年将近十代人的原始积累,如今成了整个即墨西北洼最繁盛的家族,人口旺盛,沃地千亩,可算是骡马成群,家大业大。
最令人羡慕的是刘家还有一支政府许可的民团自卫队,这可不是随便一个地主豪绅有钱就可以办的事,这说明了刘家在当地的人脉和声望。民团有五十多人枪,即墨也有几处乡镇有这种民团的,但规模不大,一般也就十几二十几人,说白了也就是某些有钱人为充面子组织的。民团的费用大半为刘家支付,剩下的一是辖区各村的惯例,另一个是上边政府拨付的官银。队长则是刘长卿的大儿子刘祖兴。
刘长卿的祖上据说有人中过举人,到了刘长卿这一辈也出过几个秀才,尽管有的功名是靠白花花的银子捐来的,刘家人还是愿意以书香门第自诩。
刘长卿的父辈哥四个,俩姑姑,到了他这里却成了单传。他自己也就生了俩儿子,老大刘祖兴,老二刘祖旺,闺女不少,生了四个。
一拉十间的祖屋比村里任何一家的房子都高大宽敞,这里不仅是刘家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整个刘家庄标志性的建筑。大门旁立着两只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有些变暗的汉白玉石狮子,张着血盆大口似乎在显示着主家的威严。
一进大门是一道影壁墙,墙的正中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周边配着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砖雕彩绘,栩栩如生。前后二十几米的院子里铺着条石和青砖,左右各有五间厢房,正中立了一堵墙,两个院子有一道月亮门可以贯穿,古人讲究东为上,所以东面的五间房自然也就成了历代族长的卧榻之地。西面五间也有大门,平时不怎么开,最东边一间被开成客房,一般得遇到有身份的客人来才可以住进去,比如过路的官员之类。中两间正房开成方间,摆放着桌椅板凳,是平时召集族人议事用的。靠西还有两间,一间做了厨房,另一间是伺候老太太的丫鬟们住的,护院们住在东屋的厢房里。几株一搂多粗的大枣树已经没人说得清是哪辈子祖宗栽下的,遇到丰收年一棵树就可以打下几百斤又甜又脆的枣子。靠西墙的地方有几颗胳膊粗的葡萄树,整个西跨院的上空几乎被这几棵葡萄树占满。
刘长卿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小哥俩住在祖屋后面,也是一拉十间,只是比祖屋略矮一些,哥俩分开,每人五间,独门独户。
在宽敞明亮的祖屋内,刘长卿端着他的水烟袋,坐在八仙桌旁的一把枣木太师椅上,半睁着眼,咕噜咕噜一口接一口的享受着大闺女送给他的水烟袋带给他的惬意。一对八哥挂在屏风一侧,时不时的叫上几声。刘长卿和那对鸟儿一样,也会时不时的和站在他身边的儿子说上几句什么,一个十五六岁的丫鬟在一边伺候。
刘长卿本人也就一米七多点的中等个,四十多岁的身子略有些发福,平日里不拘言笑,好像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既是族长又是镇长的威风来一样。
刘祖兴今年二十三,长得膀阔腰圆的,知情的都说他是典型的随姥姥门上的人。祖兴从外形上看也算对得起山东大汉的称号,只是性格略有些弱,和他弟弟祖旺的好勇斗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别看他是民团的队长,在民团里他说话都没有后来的刘祖旺说话好使。几个堂兄弟在祖旺长大之前,几乎没人在乎他这个队长,闹得最凶的当属和祖兴同一个祖爷爷的祖禅、祖让哥俩,他们串联一些旁支的兄弟曾几度提出要换掉祖兴这个说了不算的傀儡队长。
他们的理由其实也说得过去,老规矩只说族长必须是由长子长孙担任,但没说什么好事都得先由着长子长孙来。比如这个队长,如果他有能力能干好也行,没能力就赶紧给别人腾地方。
刘长卿也为这个事恼火过,即恼恨几个堂兄弟在背后教唆晚辈们胡闹也恼恨这个不争气的窝囊儿子怎么就烂泥扶不上墙。一个破队长当不当无所谓,但既然当上了就不能被人撵下来,不然他这长房的脸往哪放?
祖旺还小,虽然打架出手狠,但毕竟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刘长卿想让祖旺换下祖兴,也曾把话透给一个本家兄弟,奈何这个兄弟一直装聋作哑闭口不谈。别人不肯出来说话他自己也不好说用小儿子换下大儿子的话,刘长卿只好采用拖字诀,等着小儿子长大。好在这几年乡下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祖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些想谋这个位子的人没有正当理由也不好过于逼宫。
刘祖兴的媳妇终于生了,是个大胖小子,这可是老刘家正宗的长子长孙,也是未来刘氏族长的继任者。刘长卿高兴的不得了,改朝换代时他也没有如此兴奋过。族人和亲朋好友得知消息后陆续过来贺喜,刘长卿和刘祖兴或站或坐的就在院子里迎来送往。
祖兴的媳妇是往南三十里的七级镇七级村人,他老泰山隋素开在七级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刘长卿和隋素开是老辈们给认的把兄弟,两家结亲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不知何故,隋氏进门两年了肚皮却始终不肯给她长脸,一直就那么平平的空着,为此她可没少受族人的非议和中药汤子的折腾。
隋氏这边没有动静,后来居上的小叔子祖旺却先拿出了成绩,尽管是个女孩子,还是让隋氏着急的不行。好在乡下人有个俗语,说什么当年结婚当年孩,当年没有等三年的说法。隋氏只好一边抓紧调理自己的身子一边上香拜佛的祈祷着能在第三年到来的时候怀上孩子,现在顾不上男女了,好歹得先生一个打破外人的猜忌再说。
谁知满了三年还是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年刘长卿正准备坚决让祖兴纳妾的时候隋氏却如愿以偿的怀上了,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是偏方的功劳还是佛祖、菩萨、祖荫的功劳,反正隋氏的肚子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
秋凉下来,地里没有什么作物了,看着庄稼大丰收了的刘长卿心里又不痛快了,他搞不懂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刘家,盼了四年多,这长子长孙好容易怀上了吧,到了日子却又不肯出来。预产期都过十多天了,隋氏还是没有要生产的迹象,刘家的人又开始被这个小家伙搞的天天把心吊在嗓子眼里,唯恐有什么意外发生。
隋氏自己更是怕的不行,即怕胎死腹中,更怕肚子里怀的是个讨命鬼,搞不好临产时会把自己也搭进去,不管祖兴怎么安慰也无法让隋氏的心踏实下来。隋氏的娘家妈隋老夫人在闺女没有怀孕时到处烧香拜佛许愿,好容易盼到闺女怀孕后又到处还愿,方圆百里的庙几乎被她拜遍了。现在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吧,孩子却迟迟不肯落草她又坐不住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许愿,后来干脆就在邻村一个供奉着仙姑的砖塔前搭了一个帐篷住了进去,每日里吃斋念佛的给仙姑许着愿,全然忘了这位仙姑并不是佛家子弟。
半个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刘隋氏和肚子里孩子的消息又成了周围好事者的下酒菜,有人说:这小子肯定是属驴的,不呆满十二个月不会出来。有人说的更难听:该不会是刘家大小子不行,找驴借.的.种.吧?
乡下人说这些的时候都当笑话说,并不避讳什么。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刘大镇长那里。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总不能为一句闲话灭了谁的门吧?刘长卿只好躲着大家,反正镇上也没多少公务,后来干脆他连镇公所也不去了。
正好凑齐了十一个月,大概是胎儿自己憋不住了,想出来透透气。大清早羊水就破了,隋氏疼的杀猪般的嚎叫,叫声里透着绝望,生怕真被这孩子追了命去。
接生婆挑的是本镇最好的尤氏,从隋氏到预产期那天尤氏就被接过来时刻陪在孕妇身边,一步都不许离开。刘家有的是钱,不差产婆这几个银洋,刘长卿当时就和接生婆尤氏说了,安心的在刘家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家里若有什么事他可以派人去帮忙处理,在孩子没落草之前家里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不许她回家。
刘长卿甚至私下里还交代过尤氏,一旦生产时不顺利自管大胆动手,哪怕是开膛破肚也要保证他刘家的血脉毫发无伤的平安生下来。刘长卿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干了半辈子的接生婆自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刘祖兴到底是和隋氏做了快五年的夫妻,情分自然还是有的。那天他把老中医何老太爷请过来给媳妇诊看,到上房和老爹商量中午时留老先生吃饭让老爹作陪的事,正看到尤氏从父亲屋里出来。尤氏见到他如同做了贼一般,连个招呼都没打低着头就急匆匆的过去了。不用问祖兴也能猜到父亲会和她说些什么,他和老爹说完正事后赶紧拿着银子找到尤氏,一问,果然老爹就是那么个意思。得到确认后,祖兴求尤氏遇到万一时一定保大人要紧,切不可听他父亲的主意。
尤氏两边接了好处,不由得有些为难,思虑了一会对刘祖兴讨好般的说:“大爷,这件事您不交代我也会这样做,我是担心真到临盆了老爷派人盯着怎么办?我听说大奶奶的娘家也是有些身价地位的,亲家老爷又是咱家老爷的拜把子兄弟,依我看若大奶奶生产时能把她的父母接过来那才是最把握的。”
刘祖兴听尤氏说的有理,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大清早尤氏跑来告诉他隋氏的羊水破了,估计三两时辰内就可能生,让他赶紧想法通知他岳父岳母过来压阵。
刘祖兴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敢出去,只好去求他的堂哥刘祖禅替他跑一趟七级把他岳父母搬过来。
刘祖禅知道自己这个堂弟性格有些软,平日里在大爹面前唯唯诺诺的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可不敢为了平常争队长的那点小不快就推辞,急忙牵出自己家的大驴骡替刘祖兴报信去了。
隋素开闻讯后顾不得招待这位亲家小辈,封了十个鹰洋算是谢礼,随后就跟了来。临出门还不忘打发人备车去接陪仙姑住了半个多月的老伴,特意嘱咐下人们接到老夫人后无需回家,直接去刘家庄闺女那里就行。
隋氏生产时还算顺利,没有出现那种令人担心的场面。隋素开赶到刘家后也就是盏茶的工夫,尤氏就出来报喜了:“恭喜刘老爷,恭喜亲家老爷。大奶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七斤六两,母子平安。”
俩亲家喜得哈哈大笑,刘长卿念着喜词说道:“七斤六,家财万贯好福寿。整八斤,最低是个大将军,好,好。那咱就凑个整,小名就叫八斤吧。”
俩老头一高兴同时重赏了尤氏,刘长卿吩咐下去先摆一桌好酒他要和亲家好好庆祝一下。等亲家母赶到时,孩子已经被收拾利索。这场酒从中午开始一直喝到晚上,刘长卿一时兴起还当场就把两只八哥放了生。隋素开和刘长卿都喝得酩酊大醉,就连怎么分的手他们都不知道了。
大清朝完蛋了,小皇帝先是被袁世凯从龙位上揪了下来,后又被孙大炮的革命党赶出了北京。这个消息带来的震荡对远离京都的即墨人,尤其是最偏远的刘家庄镇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反正谁上台也得交皇粮国税,只是他们听说新党们有剪辫子的嗜好,而且还不准女人们包脚,这让老百姓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你造反也好革命也罢,我的辫子碍你什么了?一个女人家若是生在农村也还罢了,若是大家闺秀,你不许包脚,你让人家晃着个大脚丫子还怎么嫁人?有人开始瞧不起这个革命党了;你成功了你喝酒吃肉没我的份,难道你失败了我们还得跟着陪葬吗?
刘家庄的人毫不在乎的依然故我,男人们依旧甩着大长辫子满大街晃悠,女孩们照旧被父母强制着裹着小脚。
县城里有些遗老遗少们为了躲避那些革命的学生突击剪辫子,纷纷跑到了乡下。有几个在外地和即墨城里做小生意的刘家庄人也跑了回来,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也跟着他们一起涌入了刘家庄。
虽说到了晚晴这会已经没有了留发不留头的铁律,但已经习惯了二百多年的男人们却视辫子为生命,好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留辫子,根本也不知道这是满人的习惯,甚至多半人都不知道皇帝是满人还是汉人,他们只是习惯于大家都这样的装束,所以没有人会有个疑问。跑回来的人带回的这个消息真的不好,这让大家都觉得有些闹心,没几天,镇里也贴出来了要求大家自愿剪掉辫子的布告。
乡民们开始担心起来,好多人找镇长打听消息,见到镇长有人甚至还要非得亲手摸一下镇长的辫子是真是假。镇长给他们吃的也不是定心丸,只是说上面开会要求所有男人要剪掉辫子和禁止妇女缠足的事,但不是强迫,是自愿。
其实刘长卿自己也吃不准这个自愿是不是如同当时留辫子一样,是没得选的自愿。刘大镇长是读书人,他可是知道这条辫子是怎么回事,尽管他并不抵触剪掉辫子的法令,不过他也从来没有感觉有这个辫子是个什么坏事。
得不到具体指示的乡民们下地干活时开始提心吊胆起来,生怕正干着活呢,有人突然大叫着‘革命’拿着把剪刀就窜了出来。他们不是真就舍不得这个辫子,他们是害怕,小时候他们可是没少听老辈们讲过以前辫子和脑袋打架的故事,这种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扎下根来,毕竟谁也不想为了根辫子和脑袋过不去。